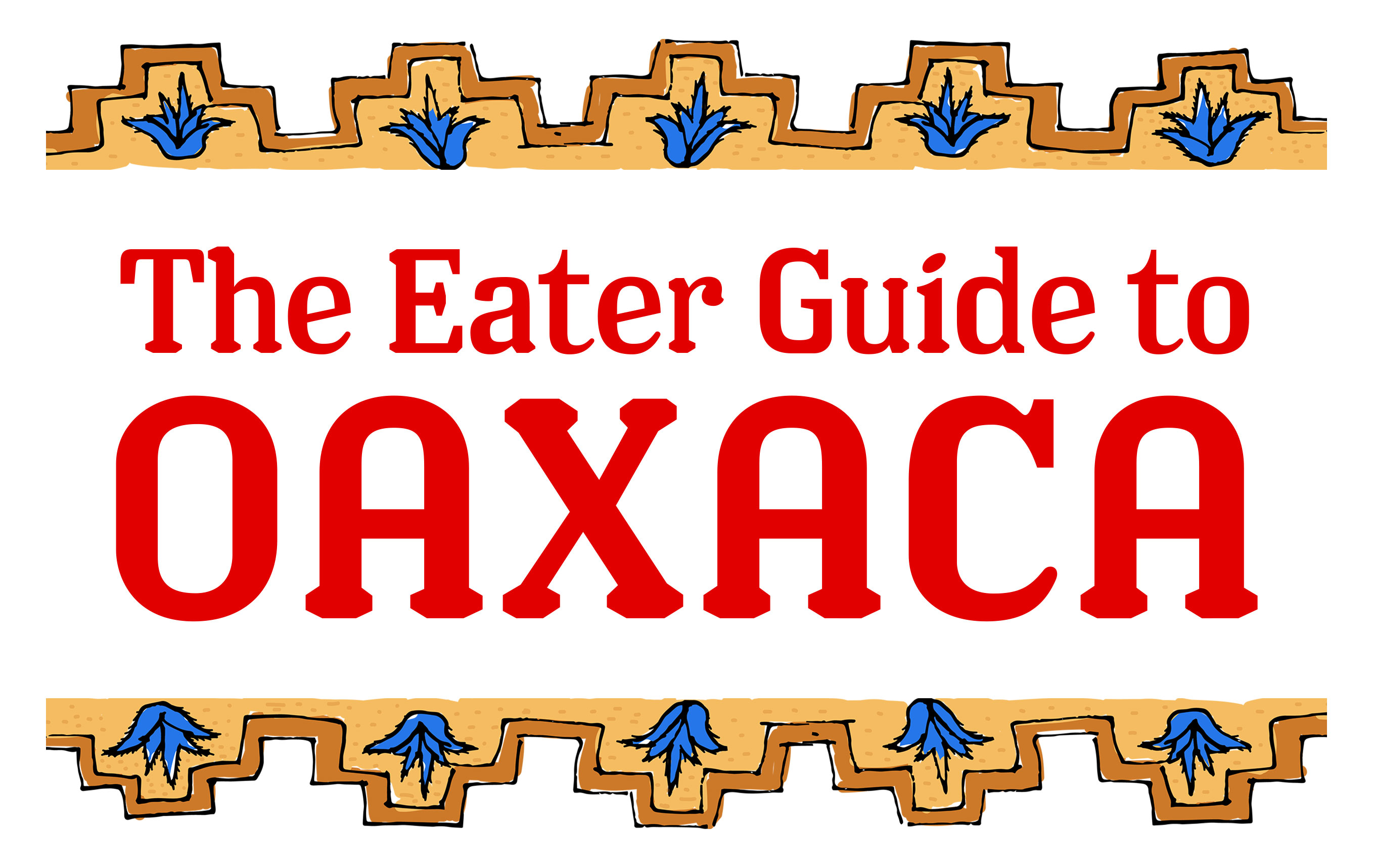“在村子裏,人們過去常說,吸辣椒的煙對身體有好處,”埃爾維亞León Hernández說。她一邊把幹的、皮厚的chilhuacle辣椒和鯷魚辣椒混合在一起,一邊從煙裏咳嗽著。她和兒子Jorge León在瓦哈卡郊區經營著一家Alfonsina餐廳,當爐火在這家餐廳的花園裏燃燒時,她用一種用幹棕櫚葉製成的escobeta不斷地移動辣椒。León Hernández正在製作黑痣,這是瓦哈卡最具代表性的痣。這是人人都在談論的一道菜,這道菜似乎有無窮無盡的本地和外國食材的組合,她已經做了30多年。
當辣椒變硬,看起來像木炭塊時,她用一塊紙板把它們從煤煤上掃到一個碗裏。她先烤其他食材,最幹的先烤:鯷魚辣椒、杏仁、浸過水的芝麻、肉桂棒、葡萄幹、大蒜、牛至葉、百裏香、丁香、孜然。一根成熟的香蕉,連皮一起放進木炭裏,放在煤塊下麵,旁邊是洋蔥、西紅柿和番茄。把這兩種辣椒的籽烤一下。香蕉和蔬菜被移走後,辣椒在她手中被捏成更小的塊兒。然後她把注意力轉向了metate。
:no_upscale()/cdn.vox-cdn.com/uploads/chorus_asset/file/23217170/elvia_jorge_alfonsina_portrait.jpeg)
阿方西納的metate是一種用河石製成的工具,用來磨辣椒和其他食材,它彎曲而笨重,據估計它可能已經使用了至少40年。她把一把辣椒放在舊石頭上,灑上水,然後用手緊緊握住滾輪,磨出少量的辣椒。這不是一個滾動的動作,而是向下推和向後拉,同時輕彈她的手腕。她知道,當混合物變得光滑時,也就是當辣椒溶入金屬酸鹽時,就做好了。
她在蔬菜上重複這個過程,然後是香草和堅果。這需要時間和體力。當她一遍又一遍地研磨這些混合物時,她回憶起在西北近200公裏外的家鄉聖多明各諾多(Santo Domingo Nundo)做鼴鼠的情景。大概會有十幾個女人帶著她們的metates站成一排,肩並肩地在石頭上磨蹭。她還能聽到風吹過樹林的聲音,她說,那時他們正在一起做鼴鼠,一起消磨時光。“我們談論生活、田地、玉米和豆子,”她說。“這是舒緩的。”
當每一種黑鼴鼠的混合物都達到了她想要的稠度時,她就在一個陶罐裏加熱豬肥肉(豬肉肥肉),這個陶罐放在幾塊磚上,在離煤窯幾步遠的地方生起了柴火。她加入辣椒混合物,然後是種子混合物,一些巧克力,和其他的。她撒上一點鹽,然後是水和雞湯,一點一點。在接下來的幾個小時裏,她不停地攪拌,鍋裏冒著泡泡、飛濺、冒煙。
當你品嚐León Hernández的黑痣(mole negro)時,它可能與蛋白質或antojito(一種以masos為基礎的零食,如tlayudas和玉米粉蒸肉)一起出現,這取決於她當天的心情,18種食材中沒有一種是突出的。她就是這麼說的。通過煤的煙霧,金屬的研磨和火的熱量,一切都成為一個。
“mole”這個詞是由納瓦特語“mymlli”,大致翻譯過來是“多水的食物”,比如醬汁或燉菜。早在洋蔥和芝麻等外國食材引入之前,墨西哥的18個民族就開始製作鼴鼠肉了。摩爾的定義技術,將辣椒和其他食材研磨在一種金屬酸鹽上,有當地的根源,這些早期的摩爾使用的是當地的東西:辣椒、西紅柿和被稱為qu精英的野生綠色蔬菜——根據當地的小氣候,各種各樣的食材,瓦哈卡有很多。今天在農村做的一些鼴鼠肉仍然像這些,許多你可能認出是鼴鼠肉的菜不一定叫鼴鼠肉;他們可能被冠以土著居民的名字或某一特定村莊的名字。
瓦哈卡所謂的“七摩爾”(negro、rojo、coloradito、amarillo、verde、chichilo和manchamantel),隨著時間的推移,包括了一些與後殖民時代更有關聯的食材:洋蔥、大蒜、芝麻和某些香料。中央山穀的許多摩爾都含有增稠劑:堅果、生的或熟的masa和玉米餅通常是土著的做法,但現在傳統廚師可能會使用麵包或芝麻粉,如果要使用增稠劑的話。作為伴奏,玉米餅是唯一必不可少的補充。“沒有標準化,”喬治在服務間隙坐在Alfonsina餐廳的一張桌子上解釋道。“沒有人能確定(某物)是否是鼴鼠。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定義。”
:no_upscale()/cdn.vox-cdn.com/uploads/chorus_asset/file/23217159/elvia_comal_mole.jpg)
:no_upscale()/cdn.vox-cdn.com/uploads/chorus_asset/file/23217154/IMG_9549.jpg)
:no_upscale()/cdn.vox-cdn.com/uploads/chorus_asset/file/23217202/IMG_9602.jpg)
廚師維羅妮卡·阿基諾·安布羅西奧(Veronica Aquino Ambrocio)在聖Martín蒂爾卡傑特(San Martín Tilcajete)的一個再林地項目的廚房工作,對她來說,鼴鼠肉意味著瓜約洛特肉湯(caldo de guajolote)的溫暖,這種深情的火雞肉湯賦予了中央穀聖安娜·澤加什(Santa Ana Zegache)的鼴鼠肉標誌性的風味。她在做黑痣或彩色痣時,會把肉湯和辣椒混合在一起。在她成長的過程中,沒有肉來配鼴鼠肉——她的家庭負擔不起——所以他們用白豆代替。在Teotitlán del Valle擁有兩家餐廳的卡琳娜·聖地亞哥(Carina Santiago)來說,摩爾讓人想起祖母把新鮮的牛至和百裏香磨在一塊金屬上做卡斯蒂利亞摩爾(mole de castilla)的聲音。卡斯蒂利亞摩爾通常與麵包一起加厚,與火雞一起食用。對於瓦哈卡州Levadura de Olla餐廳的老板塔利亞·巴裏奧斯García來說,鼴鼠意味著家人把一籃子野生蘑菇送到她家的驚喜;這些親戚們會在淩晨4點起床,收集蘑菇,製作墨西哥紅果幹酪。
換句話說,在瓦哈卡附近的餐館、住宅和市場,每個人做的鼴鼠肉都有點不同。有些人可能會使用鯷魚辣椒,而其他人則使用costeños。有些人可能會用麵包使醬汁變稠,而另一些人可能會用masa。有些人可能會把辣椒烤得更久。有些人可能會用攪拌機,而另一些人則使用metate。瓦哈卡不是七隻鼴鼠之地;這片土地上有7000摩爾。你越是試圖定義它們,就越會意識到它們無法定義。他們是一切。他們是什麼。
我第一次見到León Hernández和León在2018年底,他們一起開了Alfonsina不久。在此之前的幾年裏,她每天都在做玉米餅,並把它們和各種各樣的安托吉托一起賣給鄰居,而León則在專業廚房工作,最初在瓦哈卡之家,在那裏他學會了製作傳統的瓦哈卡菜。後來,他成為了墨西哥城Pujol餐廳不可或缺的一員。Pujol餐廳是恩裏克·奧爾維拉(Enrique Olvera)的國際知名餐廳,以“鼴鼠”(Mole Madre)和“新鼴鼠”(Mole Nuevo)聞名。
當León回到瓦哈卡時,他想和他的母親在聖胡安巴蒂斯塔拉拉亞的家中創造一些東西。他省下的每一個比索都用來購買廚房設備,用煤蓋了一個小餐廳。他們清理了庭院,增加了幾張桌子和一個室外廚房,廚房裏還有一個煤爐和一個火坑。一開始隻有母子倆,但這個團隊很快就壯大了,這一點在最近一次午餐服務前的廚房裏就能明顯看出。León的繼父馬其頓·García正在院子裏的篝火上把玉米放在一個大鍋裏進行毒化,製作明天的masa。León的哥哥Rubén是副主廚,負責為甜點剝火龍果和碾碎杏仁,而他的妻子克勞迪婭負責預訂和管理用餐區。有阿姨和堂兄弟姐妹在準備,做玉米餅,做服務員。他們都穿著寫著"家族"的t恤
長白玉米是一種墨西哥的傳家品種,是阿方西納餐廳菜單的支柱:上午,它是León Hernández餐廳comida corrida的傳統食物之一,下午,它出現在León餐廳的菜單上。León餐廳的菜單形式更自由,午餐和晚餐都有它的供應。這對搭檔從他們祖籍村莊的小農那裏獲得玉米,用於製作玉米餅、tlayudas、sopes、tamales和tostadas。但是摩爾是常數。
《鼴鼠》是一本由個人經曆和特定靈感塑造而成的活生生的文檔。León Hernández的痣靈感來自於她從小做的痣和山穀裏經典的混合混合。在她的村子裏,他們隻做一種——一種有點像科羅拉多辣鼴鼠豆的紅辣鼴鼠豆。在那裏,人們吃什麼都吃辣椒,沒有她現在用在黑鼴鼠肉裏的外國種子或香料。當León Hernández搬到瓦哈卡後,她的婆婆教她關於黑鬼和estofado的知識。León Hernández覺得它們太甜了,就按照她所在村莊的風格,用更少的糖和更多的辣椒進行了調整,創造了自己的食譜。
:no_upscale()/cdn.vox-cdn.com/uploads/chorus_asset/file/23217174/BB7BE74C_5FEB_4C89_9799_742B80E40440.jpeg)
León還記得他第一次在聖多明各吃他母親做的痣。埃爾維婭遞給他一顆茶花,這是一種現在在阿方西納當勺子用的達西裏奧的品種。鼴鼠活得很有活力。即使在那時,他也意識到這不僅僅是食物,還有其他東西:他會在生日慶典、婚禮上吃它,或者在聖聖節(Semana Santa,聖周)和蝦餅一起吃,叫做tortitas de camarón。“場合是次要的,”他說。“光是準備鼴鼠肉本身就是一種慶祝。”對於一些純粹主義者來說,León上的痣甚至可能不被認為是痣。它們是新鮮的痣,更像是前西班牙時期的痣,就像鄉村的痣,靈感來自當地的農產品:白色、綠色和黃色,通常是季節的表達,有時用yuca或pulque之類的東西製成。他在瓦哈卡的Mercado de Abastos收集農產品時想出了很多這樣的點子。就像他媽媽的痣,很辣。
León Hernández談到兒子的痣時說:“我認為它們正在發育和生長。”“他們令人驚訝。我愛他們。”
雙方都非常尊重對方的工作。他們經常一起在廚房裏:他可能會告訴她如何清洗辣椒,以最大限度地提取味道,或者解釋為什麼使用一種配料比另一種重要。她可能會教他一種特殊的方法來磨藥草。有時在廚房裏,她在攪拌他的一顆痣,而他在為她磨辣椒——所以很難區分一顆痣從哪裏開始,另一顆痣從哪裏結束。
當他在Alfonsina做他的痣時,León可以追蹤到他是如何通過時間推移來做痣的。18歲時,他在瓦哈卡之家的廚房裏,有人讓他做餐廳的鼴鼠肉,給了他大批量的食譜——餐廳一次做50公斤。他說,在那些日子裏,他沒有任何製作鼴鼠痣的經驗:女孩們在小時候就被教做鼴鼠痣,但男孩們卻沒有。他說:“我必須弄清楚。”從那一刻起,他開始對母親的烹飪更感興趣,開啟了一段永無止境的旅程,試圖了解自己是誰,來自哪裏。
當León Hernández看著她的兒子做鼴鼠時,她想起了自己20歲的時候,從她的村莊到達機場旁邊的聖胡安巴蒂斯塔拉拉亞,在前往美國的途中。León告訴我:“這本來隻是個中途停留。”“村子裏的所有人都移居到那裏。”聖多明各·諾多正在清空。León當時隻有4歲,搬到美國意味著他不會記得墨西哥或印第安印第安人。León Hernández知道這意味著什麼——不僅對她的兒子,而且對所有人。她告訴家人她改變了主意。“我們不會離開,”她說。“我們要待在瓦哈卡。”
在清晨當瓦哈卡的大部分人還在睡覺的時候,我和León一起走過Abastos市場。他解釋說,在過去,每一種蔬菜和辣椒都是某種種類在某一地區特定的小氣候中生長的傳家寶品種。但在過去幾十年的某個時刻,隨著獲得商業產品變得更容易,情況開始發生變化。村子裏的人們不再使用像panela和手工鹽這樣的東西,而是使用便宜得多的工業糖和鹽。這些不僅僅改變了鼴鼠的味道;它們正在改變整個食材生態係統以及與之相關的每個人的生計。當我們找到一群來自遠離城市的農村社區的小販時,他們把成堆的牛油果和西紅柿攤在毯子和折疊桌上。“我不得不說服我的母親開始使用西紅柿riñon,”León一邊說一邊拿著一個兩邊有凹槽的紅色大西紅柿。她習慣了買最便宜的東西。她不明白為什麼她要花五倍的價錢買一個西紅柿。”
:no_upscale()/cdn.vox-cdn.com/uploads/chorus_asset/file/23217176/IMG_9842.jpg)
對León來說,重要的是Alfonsina做出了同樣的轉變。特別是玉米,將從聖多明各諾多的小農戶那裏采購。他經常出去尋找瓦哈卡州周圍被遺忘或被取代的食材。在sierra,他發現了一個種植criollo辣椒的社區,並製作了一種煙熏辣椒醬chintextle。在海岸上,他正在采購克裏奧羅芙蓉花,並與埃斯孔迪多港的可持續漁業社區合作。在La Chinantla的叢林中,他發現有人在種植可可,而在La Mixteca,他在購買pulque和野生蘑菇。Alfonsina正在為這些類型的製作人以及他自己的家庭打造一個自己的生態係統。
回到餐廳,León正在準備他那天早上在市場上想到的一顆痣。他從沒成功過,但他對味道很有信心。還有南瓜子,他把南瓜子研磨在維生素ix裏。他把歐芹、大蒜和洋蔥切碎,把它們和整個曼薩諾辣椒一起放進熱鍋裏。曼薩諾辣椒是一種更肥、更大的哈瓦那辣椒,沒有那麼辣,但味道保持不變。幾分鍾後,他加入南瓜花。很多。sautéing後約30分鍾,它們在鍋中枯萎融化。
在攪拌機裏,他加入了一些混合物。他嚐了嚐,點了點頭。他又混合了一些,嚐了嚐,然後從鍋裏再加入一些,混合直到維生素ix開始冒熱氣。他炒了一些歐芹,把它放進攪拌器裏攪拌一分鍾,然後把所有東西都倒回鍋裏。攪拌,回到攪拌器,回到鍋裏,再放更多的辣椒:所有的東西都來來回回,直到混合物有合適的質地和味道。他遞給León Hernández一個有一些痣的甜瓜,她點了點頭。就像他媽媽的痣一樣,沒有單一的味道,但有一點辣。
:no_upscale()/cdn.vox-cdn.com/uploads/chorus_asset/file/23217216/IMG_9812.jpg)
當他在烹飪一些魚和芥菜葉時,我們開始談論Pujol著名的mole Madre, mole Nuevo菜。這可能是現代墨西哥美食中最具象征意義的美食食譜了,它是一個兩摩爾的盤子,每隔幾天就會有一個老的黑鼴鼠不斷被喂食新的黑鼴鼠,類似於masa madre(酸麵包開胃菜),上麵是新鮮的黑鼴鼠烤肉。
對於遊客和國際美食來說,Pujol菜是前衛的,它在Instagram上非常流行,但它借鑒了村莊慶祝活動中的長期傳統。在瓦哈卡,製作一顆痣通常需要5天,有時甚至更多。前幾天要準備所有的辣椒:清洗,焦化,研磨。然後是慶祝的那一天,社區裏的每個人都吃鼴鼠。但在第一次食用後的第二天,人們會在家裏重新加熱鼴鼠肉——著名的recalentado,意思是“重新加熱”——這樣才會產生更深的味道。
“我的母親告訴我這是多麼特別,”León說。“取暖並不適用於全村,隻適用於你的家人。這是更重要的。這就是Mole Madre, Mole Nuevo的概念:recalentando, recalentando, recalentando。”這種重新加熱的鼴鼠肉是傳統的,它不是為遊客準備的,而是為瓦哈卡人民準備的。隻要有痣,第二天它就會一直在那裏。
León網站稱,將新摩爾加在馬德雷摩爾之上是奧爾維拉的主意,這樣食客就可以一起品嚐兩種摩爾,品嚐隨著時間推移而產生的差異。就在那一刻,在Alfonsina的廚房裏,León有了一個主意,把他媽媽做的黑鼴鼠和他剛做的淺綠色鼴鼠放在同一個盤子裏。不過,它並不是一個疊在另一個上麵;它們是並排被鍍的。
作家兼攝影師尼古拉斯·吉爾是《拉丁美洲食譜和寫的子棧通訊新世界.Juan de Dios Garza Vela是一位專門拍攝美食和旅行的攝影師。當他不做攝影工作時,他也做插畫和壁畫。他現在住在瓜達拉哈拉,無法想象沒有墨西哥卷餅的生活。
/cdn.vox-cdn.com/uploads/chorus_image/image/70510843/metate_alfonsina.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