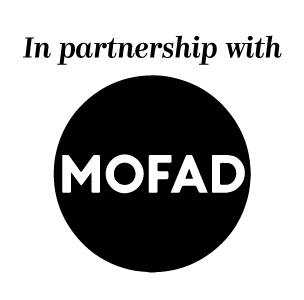不可否認,靈魂食物和南方食物根植於非洲裔美國人的經曆,但美國的黑人食物不能僅由這兩類來定義。標誌著非洲移民的運動意味著黑人烹飪對這個國家的影響要深遠得多:被奴役的非洲人帶來了作物和食物農業技能,他們將其適應了美國南部;後來,非裔美國人遷移將他們在南方發展的烹飪傳統帶到這些地區,塑造全國各地的烹飪風格.最近,來自非洲和加勒比地區的移民社區為紐約和邁阿密等城市帶來了食材和技術,為美國黑人食品的景觀增添了更多的多樣性。
晚餐係列和活動的特點是他們能夠從一個地方轉移到另一個地方,是黑人廚師、藝術家和社區組織者集中黑人烹飪經驗及其流動性質的一種媒介。在全國範圍內,這種形式,比任何一家餐廳都要多,一直是探索黑人和非洲裔美國人烹飪是什麼以及可以成為什麼的源泉,向食客介紹新的概念、食材和曆史,同時展示盤子上的文化。在過去的幾年裏,像紐約的金銀花(Honeysuckle);俄勒岡州波特蘭市的黑色盛宴;舊金山的Vegan Hood大廚;還有一些人舉例說明了黑人食物的可變性,為這個問題提供了各種各樣的答案:美國的黑人食物是什麼?
在大流行期間,這些項目可能會看起來不同或者被完全擱置,但它們仍然是討論食物中的黑人的起點。在金銀花餐廳,奧馬爾·塔特通過親密而優雅的晚餐探索了黑人文化,並特別關注南方以外的非洲裔美國人烹飪。Salimatu Amabebe在俄勒岡州波特蘭創辦了“黑色盛宴”,用食物作為媒介來慶祝黑色藝術。最後,素食帽廚師Ronnishia Johnson和Rheema Calloway是社區組織者,他們製作素食靈魂食物,並在此過程中促進舊金山社區的健康。雖然他們的工作未來可能會有一個實體中心,但他們用彈出式窗口推出的想法使他們成為持續發展的一部分黑人創新者的遺產為了更大的目標而與食物接觸。
忍冬屬植物
:no_upscale()/cdn.vox-cdn.com/uploads/chorus_asset/file/22316316/omartate_santos_12.jpg)
金銀花最初是紐約市的一個快閃晚餐係列,正如奧馬爾·塔特(Omar Tate)所說一篇文章在《食客》中,“通過食物和講故事來探索黑人生存的持續敘事。”在多道菜的餐點中,泰特將非裔美國人的曆史和文化元素放在盤子裏,比如一頓飯開始時自製的酷愛飲料(k酷愛),這是對童年的致敬,也是對黑人食物恥辱的承認,或者是“1826年左右的紐約牡蠣”(New York Oyster about 1826),這道菜參考了當年一個賣牡蠣的自由人的故事;他通過詩歌和故事敘述每一門課程。金銀花最終將成為西費城的一個社區中心融資階段他們的任務是在美國為黑人食品爭取空間。目前,泰特也是駐店主廚在石倉的藍山。
莫妮卡·伯頓:你能告訴我金銀花是怎麼來的嗎?
奧馬爾·泰特:金銀花大概有三歲了,但如果你真的想量化的話,它大概有34歲了,和我的年齡差不多。我已經做了10年或11年的廚師,主要在法國、意大利、西班牙和所有這些以歐洲為中心的廚房裏工作。我在米其林星級廚房工作過,我在酒吧工作過,我在很多不同的服務領域工作過,但沒有一個能說明我是一個美國黑人。即使在研究階段,想出金銀花的概念,我也在做南方食物的餐館工作過,而我不是南方人。
我的曾祖父母在1929年搬到費城,所以我們家已經在這裏住了三四代了。在試圖精確描述金銀花的樣子時,我不得不把我認為從廚師教育中學到的一切東西都去掉,真正考慮我的成長經曆——我吃什麼,這些東西的進化過程是什麼,這些食物來自哪裏。我成長的環境並沒有在文化上體現在很多空間中,不僅僅是食物;這不是人們在藝術中經常表現的那種東西,至少直到最近還不是。我在貧民區長大,所以我們吃的東西直接反映了當時的環境,也反映了造成貧民區的政策。這就是金銀花的由來:當你打開“貧民窟”、“兜帽”、“北方”或“城市”這些詞時,它講述了包裹裏的幾個故事。
你的一些菜肴借鑒了曆史,比如在一盤冒煙的幹草上,一盤青豆上撒著灰的火雞頸,這道菜參考了1985年的MOVE爆炸事件。你是怎麼想到這個主意的?
我對自己和我周圍的世界有強烈的考慮。在這個具體的例子中,我出生在MOVE爆炸案的一年後。但我看過一部關於它的紀錄片叫讓火焰燃燒這是(爆炸發生後)警察局長在現場下達的命令。當其他軍官說:“火已經失控了。”他們說:“讓火繼續燒吧。”我領會了那句話。擴音器裏還傳出了另一段話:“走吧,這裏是美國。”很明顯,這是MOVE組織,但也有“MOVE”,比如“讓開”。對我說"這裏是美國"就等於說"你不是美國人"它在說:“我們是美國,我們要通過燒毀這個地方來重塑這個美國。”
所有這些都造成了一種對人性的漠視和不尊重,不管他們是不是黑人——而不是說他們隻是碰巧是黑人。這種事隻會發生在黑人身上。我想從外在的角度展示盤子裏的那種審美上的漠視,但也要展示裏麵所有的細心和美味,以及豆子的烹飪方式——內在的部分是人的元素,是盤子裏的人性部分。
我把曆史作為工具,作為顏色,作為材料來講述現在和過去的故事。曆史不是我們的過去;它一直伴隨著我們。我們是否承認這一點是個問題。
從烹飪的角度來看,南方食物有一定的特點。你認為北上移民的食物可以用類似的方法提煉出來嗎,還是僅僅基於你的親身經曆?
我通常指的是北方的靈魂食物。靈魂食物不僅存在於北方,對我來說,對於那些回不了家的人來說,它是聚會的食物。我認為這就是人們從靈魂食物中尋找的體驗:它給你的基礎。靈魂食物美味可口,令人驚歎,但它沒有細微的差別和所有的特點,構成了一個人可以擁有的多種多樣的體驗與南方地區的菜肴。
靈魂食物發現自己以不同的方式呈現,這取決於當地和這些移民登陸的地方。你會在靈魂食物中發現不同的區別,通常,這些東西包括當地其他移民菜肴的部分和經曆。
如果你去洛杉磯,在通心粉和奶酪或類似的東西旁邊,會有一個充滿活力的靈魂食物版本的墨西哥玉米卷或玉米卷。同樣的道理也可以用在注入了大量意大利語的東北地區。人們吃意大利麵和火雞肉丸並不牽強。所以這是一種以靈魂食物為核心的東西的混合體,然後從其他文化中抓取混合在餐桌上。
在你的pop-up中是否出現了其他非洲僑民的元素,或者影響了你對美國黑人食物的概念?
不是很多,這是故意的。金銀花的獨特之處在於,所有的環境和圍繞食物建造的東西使它成為一種非常獨特的黑人體驗,但你不能把它歸類——我不會把它歸類——作為一種代表人類的美食。這是一種講故事的方式。我用法國、西非和意大利的技術。我盡我所能來證明我是黑人。這就是金銀花的簡單介紹。
我做我故意用一些東西,比如秋葵粉來增稠醬汁。我有意從我在旅行和研究中遇到的黑人生產者和農民那裏獲取信息。當我和我一起工作的廚師交談時,我故意不使用歐洲中心語或法語,比如我不會使用“就地安排”這個詞。這是我不得不忍受的解構的深層部分,以重建和重建一個對我來說有意義的框架,以非洲為中心,自由的。
快閃店能成為探索這些想法的最佳媒介嗎?
它沒有實體空間的限製。我不用付房租,不用付租金,我的勞動力成本很低,我們的食物成本是我想要的。我不需要盈利來確保它的存在。基本上,我不需要對資本主義感恩戴德才能讓這件事發生。
我喜歡像說唱歌手製作混音帶一樣看待它。他們沒有和唱片公司合作,也沒有付錢給某個機構。從字麵上看,這是他們的話語超過了節拍,他們以他們想要的方式來分配它,這再次說明了自由。但我從沒想過這隻是個快閃店。我的目標是申明這種體驗是有價值的,並將其與人們在Blue Hill或Osteria Francescana或其他類似的地方所能獲得的體驗相提並論,在這些地方,廚師們提供的體驗比餐品和用餐體驗本身更重要。
你如何繼續你目前的項目和社區空間的快閃式工作?
即使沒有快閃店,金銀花的價值仍然存在:以非洲為中心的價值,強調黑人經曆的價值,分享資本的價值,以及與其他黑人工匠或生產者共處的價值。所有這些都仍然存在,即使在大流行的世界裏,我不能像以前那樣做快閃。
但這場大流行真正為我做的是拓寬了我工作的價值範圍,以及它如何服務於社區的多種需求。它仍然存在於專業領域,但美國黑人或黑人人口是我的靈感,我想把它帶回家,回到現實,並了解到我可以使用所有這些關於農業采購和增長的想法來服務於我的社區的需求,並將這種經濟帶入我的社區。我還想在需要的時候做彈出窗口,但要讓它成為一種更容易理解的體驗,而不是一種藝術的、短暫的體驗。這些經曆總是有障礙。無論我走了多遠,我仍然覺得它發生在象牙塔裏。
黑色的盛宴
:no_upscale()/cdn.vox-cdn.com/uploads/chorus_asset/file/22316331/IMG_9865.jpg)
Salimatu Amabebe的黑色盛宴晚宴旨在為俄勒岡州波特蘭市的黑人創造餐桌上的空間,盡管他們已經擴展到其他城市。每一場活動都由黑人主持,並以黑人為觀眾,以一位黑人藝術家的作品為主題,提供四道菜,素食,無麩質和無甘蔗糖。在大流行期間,“黑色盛宴”開展了另一個項目,以“《給黑人的情書該公司將甜點和護理包裹寄給任何身份為布萊克的人。
Jaya Saxena:你被彈出式菜單這種形式所吸引是因為它們帶來了更多的創作自由,還是說傳統的餐廳世界有什麼讓你反感或難以接近的地方?
Salimatu Amabebe:當我搬到波特蘭時,我剛剛在柏林完成了一個專注於食物、藝術和生態的藝術家實習。我真正想做的是把食物和藝術融合在一起,嚐試坐下來吃飯的整個形式。彈出式餐廳很棒,因為你可以不斷改變形式,你可以嚐試新的想法,無論是在烹飪體驗還是坐下來用餐體驗方麵。你可以嚐試一些東西,看看什麼有用,什麼沒用,然後你的下一個活動可以結合那些有用的東西,然後嚐試一些不同的東西。我也喜歡能夠嚐試讓我興奮的新食譜,不斷地為用餐體驗注入新的能量和新的生命。
你認為食物會如何改變人們對藝術、酷兒或黑人的看法?
我的目的是把這些概念和想法放到桌麵上,讓人們自己討論、思考和處理,達到他們想要的程度。餐桌真的很平易近人;感覺人們更舒服了。我們在《黑色盛宴》中所專注的是創造一個以黑人為中心的空間,但同時也向所有人開放。據我所知,作為一個白人在那個地方的經曆有點不舒服,但你也可以吃到非常美味的食物。
它在玩弄那種不適,然後滋養人們,讓人們感到不適。在一個不是為你設計的、不是為你這個白人設計的空間裏感到不舒服是可以的。對白人來說,了解這種經曆很重要。與此同時,對黑人來說,擁有所有這些以我們為中心的空間,以我們的社區為中心,讓我們成為優先考慮的人,這是非常重要的。
在製作《黑色盛宴》的過程中,你有沒有學到一些自己沒有預料到的東西?
我的一個白人朋友說,她需要在這個領域小心行事。我們對把黑人的經曆等同於白人的經曆不感興趣。我們對扮演一個黑人是什麼樣子不感興趣。這根本不是我們的目標。但我認為以黑人為中心,以黑人社區為中心的一個副作用是,非黑人也將不得不與他們自己在這一切中的角色抗爭。輕手輕腳,高度自我意識的一部分是黑人經常有的經曆——不確定,[想知道]“這真的是為我準備的嗎?”或者明知它不適合我,但還是選擇買了一盤。
你說不想成為黑人經曆的刻板印象,你做的食物是素食,無麩質,無蔗糖。我認為不幸的是,在美國關於黑人食物的主流假設是它不是素食。你對擴大黑色食物的定義有什麼想法,或者為什麼這個假設一開始就是錯誤的?
黑人食品仍在被定義,而且很可能永遠被定義和重新定義。美國黑人,南方美食,或靈魂食物,可能以不超級素食主義者而聞名,但也有很多植物性靈魂食物餐館。隨著我們意識到有多少人有飲食限製,這變得越來越受歡迎。我感興趣的是製作很多人都能吃的食物。如果我不去迎合很多不同的飲食限製,事情會容易得多,但這些也是我所有的飲食限製。如果我在為別人做食物,如果我也能吃到就太好了。
對於黑色盛宴來說,所有這些食物都是關於藝術的。創造菜單的實踐變得有些精神和模糊,這種自由聯想的遊戲。這項工作突出了什麼?什麼能引起我個人的共鳴?我如何看待這一點在食物中的體現呢?這是如何反映在風味和質地上的呢?這是一種超越分類的東西就這道菜的根源而言。
你想如何在未來繼續使用這種格式?
我是處女座,有太多的獅子座在他們的圖表,我帶來的能量。我有很多計劃,但也完全不合理。我現在的夢想是為《黑色盛宴》擁有一個永久的空間。我們有一個商業廚房,店麵零售,這樣人們可以進入一個有戶外用餐區的空間,也有一個居住空間,這樣我們可以支持藝術家的藝術實踐。我認為《黑色盛宴》將呈現出一個多學科的空間。我很想為黑色盛宴擁有一塊土地。
我想創造一些可以傳給年輕一代的東西。《黑色盛宴》並不是關於我或我的作品。這是關於創造空間和自由,我可以離開,有一天其他比我年輕和聰明的人可以接管。在我的生活中,我也有我想做的事情,除了黑色盛宴,但我認為這類工作是我將永遠參與的事情。這種互助項目是我想一直做到死的事情。
素食帽廚師
:no_upscale()/cdn.vox-cdn.com/uploads/chorus_asset/file/22316356/_AAL7752.jpg)
三年前,羅尼西亞·約翰遜(Ronnishia Johnson)和蕾瑪·卡洛韋(Rheema Calloway)開始在舊金山灣景社區以“素食帽廚師”的名義提供素食靈魂食物。他們的素食版本,如通心粉、奶酪和炸雞,一直很受歡迎,而且他們的菜肴種類還在不斷擴大。但約翰遜和卡洛維首先是社區組織者,他們的快閃店有一個更大的使命:為被剝奪權利的社區增加健康教育和獲得健康食品的機會。在大流行之前,他們在大型活動中提供食物,但這些天,他們每周在整個灣區提供食物。
埃拉紮·桑塔格:我希望你能告訴我一些關於你的快閃店和你是做什麼的。
卡羅威Rheema:我們喜歡說社區選擇我們是因為我們是社區組織者。我們在社區中所做的一些關於食物公正的工作已經告訴了我們現在的方式。我們開始做彈出式廣告,主要是想讓社區了解舊金山存在的食物差異。我們都來自被認為是食物沙漠的社區:我們喜歡稱之為“食物隔離”,因為我們的社區缺乏健康食物的選擇。我們已經能夠廣泛地接觸我們的社區,並向他們介紹那些通過吃健康食品治愈自己的人,我們在社區中發起了關於治愈兜帽的活動。
你一直認為食物是社會正義的一部分,也是在你的社區中尋找安全感的一部分,但這是什麼時候真正轉化為開始素食帽廚師的?什麼時候開始意識到這實際上是你工作的中心,而不是邊緣?
Ronnishia約翰遜:2017年,我在Instagram上創建了一個Instagram,重點介紹了我們個人的飲食轉變,因為當我們在做這些組織工作時,我們發現如果你改變了你的飲食方式,它就會開始改變你生活的其他方麵。我們正在進行一場關於我們如何飲食的個人旅程,然後Instagram變得超級受歡迎,我們創建了一個名為素食帽廚師的頁麵。
我從沒想過要做生意。這就是它的瘋狂之處,這就是為什麼Rheema說社區選擇了我們。我們有一個Instagram主頁,開始有一些粉絲,我們的一個朋友有一個活動,廚師退出了,她說,“我知道你不是專業人士,但你介意為我做一個活動嗎?”那時候,我們有個搭檔,我在烹飪學校讀書的表弟。所以,我說,“好吧,我們試試吧!”為什麼不呢?”在我們的第一次活動中,我們為200人做飯,它非常受歡迎,從那以後,它的需求一直很旺盛。我們從沒想過這能成為一門生意,但在第一次活動之後,我們就覺得,“好吧,我們真的在做一些事情。”
主流媒體對純素食主義的描述往往是壓倒性的白人,但純素食主義並沒有天生的白人特征,而且它在很多方麵都是其他文化的核心。當你開始接觸素食烹飪,但也堅持靈魂食物時,你對素食主義作為黑人飲食文化的一部分的願景和理解是如何增長或發展的?
RJ:這是授權。這是我們的很大一部分——將食物與我們的文化融合在一起。有很多神話,特別是在我們的社區成長,素食主義不適合黑人。雖然我們覺得舒服的烹飪是靈魂食物,但我們也去過很多不同的地方。作為兩個來自兜帽區女孩,在建立兜帽素食廚師的過程中,我們去了牙買加,我們去了巴拿馬,我們去了所有這些不同的地方。
到社區以外的地方旅行拓寬了我們的視野,讓我們了解到非洲僑民和來自非洲的人們是如何相互聯係的。有些人和我們長得很像,但不一定說同樣的語言。盡管文化不盡相同,但你會在音樂或人們的長相、舞蹈風格,尤其是食物上看到許多相似之處。比如,很多美國黑人會做什錦飯,什錦飯和什錦飯或海鮮飯非常相似。
當我們去牙買加回來的時候,我們打算去舊金山的不同餐館嚐試不同的食物,因為在這裏,我們完全沒有接觸到這些。知道植物曾經是我們很多人的傳統飲食,那真是一個頓悟的時刻。我們傾向於在所有油炸食品周圍談論靈魂食物,這直接反映了我們的壓迫:擁有殘羹剩飯的想法,並能夠將它們變成美好的東西。但你也會看到很多植物和我們與很多植物性食物的聯係。我們想用我們的食物作為一個話題來揭穿一個神話,即素食主義與我們的文化無關,而它確實與我們的文化有關。
當你計劃菜單並推進這個項目時,你們倆在將這些傳統的靈魂食物改造成素食主義的同時又讓你的客戶群感到熟悉時,是否麵臨著某些挑戰?這個過程是怎樣的?
RC:主要是在調味料中。我們選擇了一些祖母們做的傳統食物,並做了很多研究,看看什麼樣的蔬菜能保持這樣的一致性。說到雞肉,我們愛上了菠蘿蜜。我們經曆了祖母們油炸或烹飪的傳統做法,然後開始學習更多不同的技術,比如使用斯佩爾特粉或鷹嘴豆粉。然後,我們專注於使用我們的傳統調味料,但尋找不同的新鮮草藥來調味我們的食物。這需要大量的試驗和錯誤,但我們基本上都是在家裏吃主食,然後想辦法把它們變成更健康的替代品。manbetx万博软件
RJ:人們經常想讓我們做快餐,而我們的目標和使命就是確保我們能做出既美味又能滋養靈魂的食物。這很有挑戰性,因為舒適的食物很棒,但我們想確保我們繼續宣傳自己,讓人們知道,如果你需要健康的食物,你可以來找我們。
這些天你在喂誰?
RC:最近,我們有很多素食主義者,但一開始,很多人對嚐試新事物感興趣,在自我探索的旅程中,試圖治愈自己,那些對健康有恐懼的人。我們接觸過的很多人都不是素食主義者,他們隻是想進來看看是怎麼回事。
RJ:大部分都是過渡素食主義者。人們會說,“我正在嚐試”或者“這是我第一次吃素食。”然後,我們會看到他們成為回頭客。
你對未來有什麼計劃?
RJ:我們今年的目標是用我們的博客和YouTube做更多的在線食譜,同時放棄我們的食譜。我們有自己的招牌醬汁,我們經常用它來做po ' boys,現在我們已經把它裝瓶了。我們希望通過提供健康食品來盡可能地飽和市場。
我們還和一個叫Cat Fitness的年輕人合作,推出了我們稱之為“治愈兜帽”的節目。我們訪問了三個不同的社區——灣景、西奧克蘭和裏士滿——在那裏,我們與社區花園合作,贈送農產品,也有很多演講者談論健康和植物性飲食,我們為社區贈送了200到300頓飯。我們最近與Aspire公立學校建立了第一個合作夥伴關係,我們在那裏做了一個在線版本。我們希望獲得更多的資助和支持,以便今年也能完成這一工作。
你的工作仍然是為社區提供服務。作為一家快閃店,也許比實體店更靈活一點,是否有一些方式讓你能夠探索更多的領域,而不是以更傳統的餐廳空間開始?
RJ:長期關注我們的人會問:“你打算什麼時候開餐廳?”但如果我們進去開了一家餐廳,我們可能會在很多方麵限製自己,限製我們能接觸到的人。我們的醬料訂單幾乎覆蓋了每個州。我們的社區參與很多都是圍繞著我們是誰,而在圍繞素食主義的對話中卻缺失了這一點。
人們很樂意支持黑人素食企業,但我們非常公開地說,“這是為了社區,由社區,為我們。”有了快閃模式,我們可以去不同的社區,談論我們是誰,也可以更靈活地走進人們的家中或提供健康教育。如果我們在一家實體店,說實話,我們每天都會在那裏,隻提供飯菜。
主要圖片圖片來源:Klaus Vedfelt, Vegar Abelsens,常綠星球通過Getty Images
尼爾·桑托斯他是費城的一名編輯和商業攝影師。切爾西Kigano她是一位藝術家、作家和教育家,住在舊金山灣區。Michelle K. Min是舊金山的一名美食攝影師。
/cdn.vox-cdn.com/uploads/chorus_image/image/68861625/MOFAD_Lede_PopUps.0.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