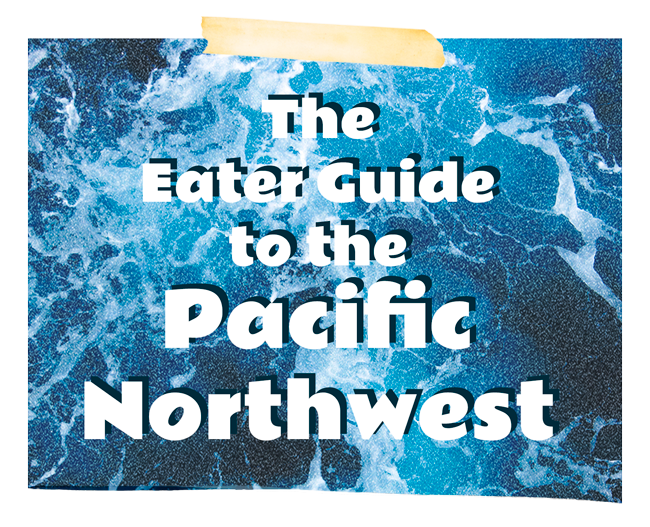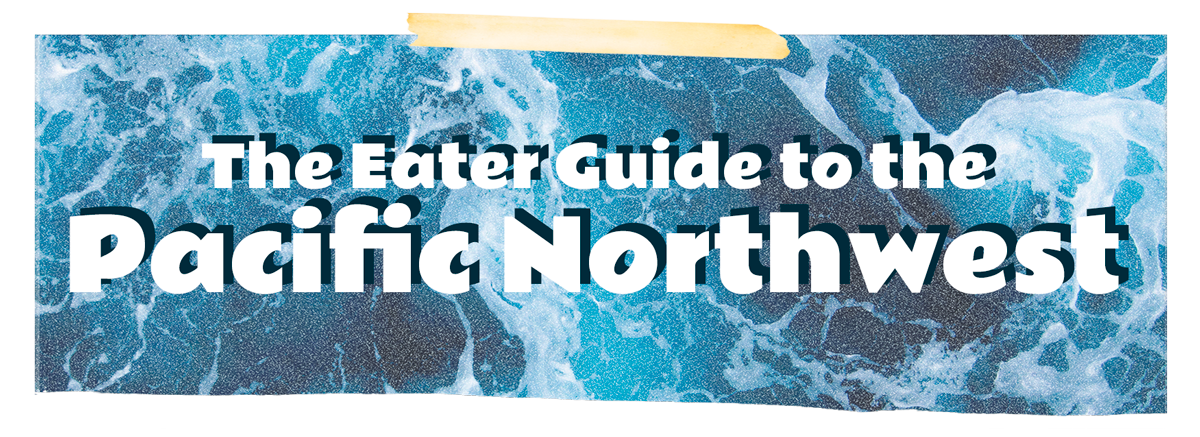在這個陽光明媚,華氏55度的周二到了三月份,整個西雅圖就好像都在度假。有推著嬰兒車的媽媽,有賣熱狗的小販,還有成群的青少年擠在城市的海濱。我聽到遠處的海鷗聲,那微弱的聲音、鳥兒和汽車緩緩駛過尋找停車位的聲音——但我看不到它們。我繼續走,經過水族館,一些紀念品商店,最後是一家糖果店,最後到達了54號碼頭。我發現,海鷗們在海濱找到了最好的聚集地:伊瓦爾蛤蜊餐廳外的海鮮酒吧。
伊瓦爾餐廳的創始人伊瓦爾·哈格倫德(Ivar Haglund)正在給饑餓的海鷗喂薯條的雕像矗立在餐廳外。幾十年前,附近的一家企業張貼告示,要求人們停止喂這些鳥,由於遊客的好意,它們變得有資格和暴躁。但哈格倫德在魚吧的戶外休息區附近貼出了自己的標語:“歡迎海鷗!歡迎海鷗愛好者來喂有需要的海鷗。”這個標誌的變體直到今天還在那裏(還有一個警告,不要喂任何進入有遮蓋的進食區域的鴿子或鳥類)。
上次我來這裏的時候,我媽還住在西雅圖,那裏一片漆黑,空蕩蕩的。但現在,多虧了一個6.88億美元的項目為了讓海濱更適合行人和遊客,這片區域幾乎認不出來。這座城市正在拆除舊的阿拉斯加大道高架橋,這是一條高架高速公路,將西雅圖市區與河水分隔開來,給這個曾經熙熙攘攘的地區蒙上了一層陰影。停車場正在被更多的綠地、自行車道所取代,從派克市場到海濱其他經典景點,如水族館、摩天輪和數不清的t恤店,也變得更加便捷。
:no_upscale()/cdn.vox-cdn.com/uploads/chorus_asset/file/16303599/Eater_Ivars_Story_6.jpg)
新老派係在一起,形成了一種令人不安的僵局。人們站在人行道上,伸出手機,記錄街道對麵高架橋的拆除過程。我和他們站在一起,看著機器碾碎混凝土就像在咬基礎設施一樣。你很少能看到一個城市決定自己想成為什麼樣子,而西雅圖希望它的居民感覺自己擁有像紐約這樣的特大城市的所有優勢,而不是被困在灼熱的混凝土人行道和建築物之間。旅遊委員會甚至試圖為它創造一個術語——“大都會自然”,指的是“晴朗的天空和廣闊的水域與快節奏的城市生活的融合”。居民嘲笑的口號但人們還是不斷地搬到那裏。今天的西雅圖是一座科技城市,這裏的水給人的感覺不過是一個拍照的好地方。罐頭廠和漁業供應公司曾經在這些碼頭上租用場地,現在隻能在水邊供應海鮮的餐館裏度日。
當我走過去點餐的時候,“伊瓦爾魚吧”的霓虹燈下擠滿了人。菜單是用仿黑板的風格寫的,有人在櫃台下麵的小瓷磚上用模板印出了“海鮮”兩個字。我又餓又興奮,這是我從小到大第一次去伊瓦爾餐廳。然而,我不禁擔心這碗雜燴湯可能不如我記憶中的那麼好;當你把它們留在過去的時候,事情有時會變得更好。
:no_upscale()/cdn.vox-cdn.com/uploads/chorus_asset/file/16303654/Acres_c50s_w_Star_Sign.jpg)
伊瓦爾的蛤地一直自20世紀30年代末以來,就以這樣或那樣的形式出現在這裏。這是第一家在全州範圍內發展起來的連鎖店,在華盛頓各地有21家海鮮酒吧和另外兩家坐下來吃飯的餐廳。在過去的80多年裏,伊瓦爾餐廳已經贏得了作為太平洋西北地區一家餐館的地位,但以高昂的價格(一份三文魚凱撒沙拉25美元,一份龍蝦尾衝浪和草皮牛排68美元)給人感覺像是遊客的地方。那些知情的人會在餐廳旁邊的無電梯櫃台點餐,然後在附近的許多桌子中選擇一張用餐(有蓋的和無蓋的,所以沒有人需要擔心太平洋西北地區頻繁的降雨會導致食物變濕)。
人們來到伊瓦爾的魚吧,因為他們提供所有你想在海濱吃的東西:雜燴湯、海鮮雞尾酒和炸魚薯條。伊瓦爾的炸魚薯條又輕又脆,麵糊和鱈魚片並沒有像許多劣質版本那樣分開;人們幾乎可以想象這些鱈魚帶著鬆脆的麵包皮在海洋中遊泳。
這家酒吧提供白雜燴(裏麵的培根剛好可以提味,但又不會太多,讓你覺得自己在吃培根雜燴,還撒了一點蛤蜊)、煙熏三文魚雜燴,或者西紅柿做的紅色雜燴。我是雜燴濃湯的純粹主義者;我總是選擇經典的白色。盡管大多數人把雜燴濃湯和新英格蘭聯係在一起,但西海岸為保持雜燴濃湯的流動已經做了很多工作。舊金山可能增加了酸麵包碗,但太平洋西北地區的冬季潮濕,貝類繁多,激發了厚毛衣和熱雜燴——無論是用蛤蜊還是同樣豐富的煙熏三文魚做的。在海濱還有很多地方可以買到雜燴湯。但對我來說,伊瓦爾的版本是家的味道。
9歲時,我和家人搬到了普吉特灣(Puget Sound)的惠德比島(Whidbey Island),那裏距離西雅圖有一個小時的車程和渡輪。我們的房子被木瓦和紫藤覆蓋著。我們有一塊牧場,裏麵有羊和一隻孔雀,它喜歡在早上6點的時候坐在我媽媽和繼父的窗外大聲鳴叫。我想,音響效果非常棒。
那三年是我小時候在一所房子裏住的最長時間。惠德比的房子感覺就像一個神奇的地方,充滿了記憶,就像一片常春藤交織在一起,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厚。我的方向感很差,我一直認為,至少部分原因是由於我的童年時期經常搬家——離婚和互聯網繁榮和蕭條的結果。在我們又出發到別的地方去之前,我還沒有時間弄清楚自己的方向。
:no_upscale()/cdn.vox-cdn.com/uploads/chorus_asset/file/16304022/Eater_Ivars_Story_12.jpg)
:no_upscale()/cdn.vox-cdn.com/uploads/chorus_asset/file/16304025/Eater_Ivars_Story_1.jpg)
海濱的伊瓦爾海鮮酒吧今天人手不足,店員讓顧客上前先點油炸食品,然後再點其他的。這是一個令人困惑的係統,但它最終是有效的。我點了一種叫“蛤蜊甘露”的東西,想象著它像牡蠣射擊酒一樣端上來。櫃台後麵的夥計喊出我點的菜:“三塊鱈魚加薯條!”海鮮雜燴濃湯的杯!然後低聲補充道,“還有蛤蜊的花蜜。”
20世紀70年代,哈格倫德為蛤蜊甘露做廣告時宣稱,男人要點三杯以上的蛤蜊甘露,必須得到妻子的允許。蛤蜊的花蜜,原來是一種無法控製的春藥。蛤蜊不通過交配來繁殖,難道它們隻是兩個貝殼,裏麵裝著一生被挫敗的性欲嗎?
花蜜裝在紙杯裏,就像人們通常喝咖啡或滾燙的茶時喝的那種東西。花蜜主要由蛤蜊肉湯、香料和黃油組成,味道清淡豐富,鮮味十足,但沒有肥豬肉湯的厚重口感。它是美味的。在喝完雜燴湯和薯片等多道魚味的味蕾後,我嚐了好幾次,以確定我品嚐的是甘露。
:no_upscale()/cdn.vox-cdn.com/uploads/chorus_asset/file/16304059/Ivar_Sitting_on_Field_of_Clams_2.jpg)
宣傳蛤蜊花蜜是春藥是哈格倫德一直在做的噱頭。1947年,一輛裝有玉米糖漿的鐵路油罐車破裂,黏糊糊的糖塊滑到了海濱。哈格倫德穿上一雙短靴,從廚房裏訂了一大堆煎餅,然後趟著水走到街上。當報紙送來的時候,他們發現他被糖漿包圍著,用勺子舀著他的早餐。他的一張照片通過新聞通訊社傳到了世界各地的報紙上。在高架橋開業的前幾天,哈格倫德雇了一個銅管樂隊在“蛤蛤英畝”外麵演出,並邀請所有人幫助他感謝這座城市在他的餐廳外修建了“有頂停車場”。
哈格倫德還經常意外地涉足當地政治。1976年,他買下了西雅圖的第一座摩天大樓史密斯塔(Smith Tower),並在塔上放飛了一個16英尺高、形狀像鮭魚的定製風罩。當市政府試圖讓他以違反法規為由將其撤下時,他以糟糕的詩歌形式進行抗議。支持者(甚至是市政官員)用詩句表達了他們的觀點。輪到哈格倫德發言時,他敦促市政府“考慮到所有這些免費宣傳”,不要太快做出決定。董事會批準了三文魚。
伊瓦爾餐廳是唯一一家餐廳我能產生懷舊之情的東西。在我成長的過程中,外出就餐是在特殊的場合——假期或生日——但在伊瓦爾餐廳,我成了常客。每次我們離開惠德比島去購物或去西雅圖IMAX電影院看電影時,我們都會乘坐渡輪,在距市區約一小時車程的Mukilteo終點站下車。在我們回家的路上,我通常已經餓壞了,如果要排隊才能回到渡輪上——這在糟糕的日子裏可能要花上一個小時——我的父母就會給我一些錢,讓我走到伊瓦爾餐館去買點東西。當時的Mukilteo Ivar’s餐廳和現在一樣,在海濱有一家餐廳,可以看到惠德貝島(Whidbey Island)的景色,還有一家海鮮酒吧,有一樣東西是其他餐廳無法提供的:軟質冰淇淋。軟湯和雜燴湯看起來像是奇怪的同桌(我的天,奶油),但對一個饑餓的10歲孩子來說不是這樣。
像這樣的連鎖店,已經存在了幾十年,給了我們重複的奢侈——吃同樣的東西的體驗,你成長為一個不同的人。這就是為什麼即使是一碗簡單的濃湯加冰淇淋也能成為個人變化的晴雨表。這也是我喜歡吃蛤蜊的原因。
:no_upscale()/cdn.vox-cdn.com/uploads/chorus_asset/file/16304065/Eater_Ivars_Story_32.jpg)
我已經有10年沒去惠德比了,盡管三年前我從東海岸搬回了波特蘭。從我現在住的地方開車到島上隻有四小時的路程。我母親最近搬回了惠德比,多年前她和撫養我長大的繼父不再說話了。他們離婚時我17歲。如今,他住在西雅圖;她,還有一個小時才到。當我和別人談論他的時候,我仍然叫他我的繼父,盡管嚴格來說這不是真的。形容家庭的詞太多了,而形容那些即使與你沒有血緣關係也不離不走的人卻少之又少。
與他的關係有時會讓人感覺不穩定,就像一個鬆散的結,我不想把它拉得太緊。我從來沒有一次去看他和媽媽,即使他們都住在西雅圖。我知道我會因為花了一個人的時間去拜訪另一個人而感到內疚。他們住得那麼近,去西雅圖卻見不到他們倆,也感覺像是冷落。所以,我根本就沒去——沒去西雅圖,也沒回惠德比島。
一項關於伊瓦爾的報道任務似乎成了我去見他們兩人的借口。當然,我可以早點起床,開車去西雅圖,吃飽魚和雜燴湯,然後在睡覺前回到波特蘭。但我卻花了一周時間。在Mukilteo Ivar 's吃完飯後,我問我媽媽是否可以去惠德貝拜訪她。然後我問我的繼父,當我去海濱的伊瓦爾餐廳時,我是否可以和他一起住在西雅圖。當然,他說,隨時奉陪。
當我到達時,他似乎很高興見到我,盡管最近我發現我們經常有一個月甚至更長時間沒有通電話。我在這裏待得太久了,不做報道就走了嗎?我提議和他在伊瓦爾餐廳共進午餐,但他已經不怎麼吃肉或乳製品了,而且他還得工作。“我明白,”我說。我對自己的失望感到驚訝。我在伊瓦爾54號碼頭海鮮酒吧加入了鷗群,這是一群鷗的聚會。
今天,就像在伊瓦爾餐廳的其他許多日子一樣,孩子們把規定的食物扔給海鷗,它們俯衝下來從小手裏搶薯條和魚。很難分辨孩子們的尖叫聲從哪裏開始,饑餓的海鷗的叫聲從哪裏開始。周圍的孩子也在做同樣的事,我把剩下的薯條一次扔一個,甚至拿出一根去喂鳥,我有一種奇怪的感覺,就像過去和現在發生了碰撞。在我長大的過程中,我每年去看我爸爸一次,他會在舊金山機場出現,包裏裝著一袋麵包,直接帶我去美術宮喂鴨子。後來我才知道給野鳥喂麵包是讓它們生病的好方法。我停止喂鳥是因為它可能會殺死它們,還是因為我想把它留在記憶中,我不確定。伊瓦爾餐館裏的海鷗張開它們的大嘴,朝我尖叫,但聲音不會太大。有時我能感覺到一隻在我頭頂盤旋,翼尖沙沙作響。我一次都沒被拉過屎。
:no_upscale()/cdn.vox-cdn.com/uploads/chorus_asset/file/16303617/Eater_Ivars_Story_30.jpg)
在我一個人去伊瓦爾家之後我回到繼父家過夜,第二天早上離開去惠德貝。在上渡輪之前,我在Mukilteo Ivar 's吃了點東西。這次不是海鮮酒吧,而是旁邊的伊瓦爾餐廳(Ivar’s restaurant)。當我們住在島上的時候,我從來沒有去過那裏——家裏總是有食物等著我們去那裏。manbetx万博软件
在很多方麵,Mukilteo Ivar 's和所有老派海鮮店沒什麼兩樣。牆壁被木頭覆蓋,浴室門有舷窗。我聽到揚聲器裏播放著柔和的爵士樂,偶爾還能聽到冰水倒進某人杯子裏的叮當聲。空氣中有一股來自服務員端到每張桌子上的新鮮麵包卷的酸味。我的服務員很友好,看起來和我媽媽年齡相仿。她端出6隻半殼的胡德運河生蠔,當我告訴她它們很美味時,她很高興。她告訴我,她在同一條河邊買了一棟房子,打算在幾年後退休。這是太平洋西北夢想:森林中的家園,後院的牡蠣床。
哈格倫德在大蕭條前一年獲得了經濟學學位。他沒有進入金融業,而是依靠從父親那裏繼承的房子出租所得的收入,成為了一名民謠歌手。他在西雅圖各處表演,經常帶著吉他和即興歌曲在他在西雅圖海濱開的水族館(他的表兄弟在俄勒岡州開了一家很成功的水族館,建議哈格倫德試一試)周圍徘徊。後來,哈格倫德在KJR有了自己的15分鍾廣播節目,並最終成為當地一個兒童節目的固定成員,隊長普吉.
他開始寫關於海洋生物的歌曲,如《向大比比魚致敬》或《快跑,蛤蜊,快跑》,這些歌曲實際上是關於人們捕捉並吃掉它們的。(大比利亞魚之歌的其中一段是這樣唱的:“烤它、煮它、炸它,無論你怎麼嚐試,它都是一場美食盛宴。”)他唱過這些和其他關於普吉特灣的歌,但哈格倫德最喜歡的永遠是《老定居者》——這是一首淘金者的歌,據說他是從拜訪的音樂家那裏學來的,他們的名字是皮特·西格爾和伍迪·格思裏。
:no_upscale()/cdn.vox-cdn.com/uploads/chorus_asset/file/16303591/Ivar_with_Guitar_at_Aquarium.jpg)
哈格倫德似乎滿足於他的水族館和音樂事業,直到他注意到一個尚未開發的市場。水族館的遊客,也許是在把他們的貨物運到海濱的船上聞到空氣中的魚味,經常問哈格倫德他們在哪裏可以吃點東西。於是,他在1938年開了一家炸魚薯條店,並最終將其擴大為自己的餐廳,他在1946年以《老定居者》(The Old Settler)中的一句台詞命名為“蛤畝”(Acres of Clams)。人們稱他為“海濱之王”,因為他聰明的行為和慷慨。1964年7月4日,當該市幾乎取消了7月4日的展覽時,哈格倫德出麵讚助,並一直讚助到2008年。1985年,當他去世時,他把公司交給了值得信賴的員工,並捐出了他的遺產,史密斯塔的三文魚紛紛下半旗。
就像在西雅圖海濱我對一個已經不存在的地方有記憶。我不知道是我記得的部分發生了變化,還是一切都變了。幾十年是漫長的,特別是對西雅圖和南惠德比之間的路線上的地方。前者越來越富有,這要歸功於微軟、亞馬遜等公司,以及它們給這座城市帶來的科技繁榮。每個人都說,南惠德比越來越貴,越來越成為有錢買第二套房的西雅圖人的度假勝地。我記得有一家叫“Neener Neener Weiner”的餐廳,我們從未在那裏吃過飯,但它的招牌卻讓人難以忘懷,因為你可以從Mukilteo賽道上看到它的招牌。我和10歲的朋友們總是嘲笑它的名字。現在它不見了,早就不見了,但在我去伊瓦爾餐廳的路上,我還能看見一個男人吃著巨大熱狗的雕刻雕像斜倚在外麵。
:no_upscale()/cdn.vox-cdn.com/uploads/chorus_asset/file/16303664/Eater_Ivars_Story_20.jpg)
現在,我還坐在Mukilteo Ivar 's餐廳的一張桌子前,啃著盤子裏剩下的炸魚。我拒絕了甜點菜單,而是走到外麵的海鮮酒吧。與54號碼頭的魚吧相比,這家魚吧單調而實用,可以輕鬆地成為棒球場的櫃台服務台,就像在渡輪上一樣。在我住在島上的20年裏,這裏是否發生了什麼變化,我不知道。我點了一個兒童甜筒,一個漩渦——我經常點的,雖然我不再是這裏的常客了。海濱的空氣中突然擠滿了海鷗,我在想是不是渡船攪動了水裏的魚。這些海鷗在不捕食人類殘羹剩飯的時候吃什麼呢?在一片混亂中,我看到一個穿著白色衣服的廚師,從碗裏往水裏扔東西。他在喂海鷗,甚至在這裏。這是伊瓦爾的傳統,謝天謝地,有些東西永遠不會改變。
兩小時後,我又會回到島上。當我見到母親時,她問我的第一件事就是:“你還記得什麼?”我被這個問題,被她想和我分享一些東西的渴望所征服。我沒有回答,而是告訴她這不是一個很好的答案。“如果有人讓你記住你生命中三年來的每一件事,你會有什麼感覺?”我也有同感。“我記得很多事情。”我知道,但我很少告訴她。我都不知道該從何說起。
我10歲的時候,就在我們全家最後一次離開太平洋西北部的前幾年,我在惠德比島的才藝表演會上表演。我不記得這首歌是怎麼選的,也不記得為什麼我決定在一個巨大的禮堂裏清唱這首歌,但我高唱了《老定居者》。它講述的是一個疲憊的淘金者,他看到許多同行的淘金者遠離家人,最終陷入貧困。“我下定決心去挖掘一些更確定的東西,”這首歌是這樣唱的。於是他放下了采礦裝備,走到普吉特灣,在那裏他終於感到快樂,“不再是野心的奴隸”,周圍不是黃金,而是大片美麗的蛤蜊。
Tove Danovich是一名自由記者,前紐約人,現居住在俄勒岡州波特蘭市。在推特上關注她,@TKDano.
勞倫·西格爾是西雅圖的一名自由攝影師。
Lesley Suter編輯
/cdn.vox-cdn.com/uploads/chorus_image/image/63954122/Eater_Ivars_Story_42.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