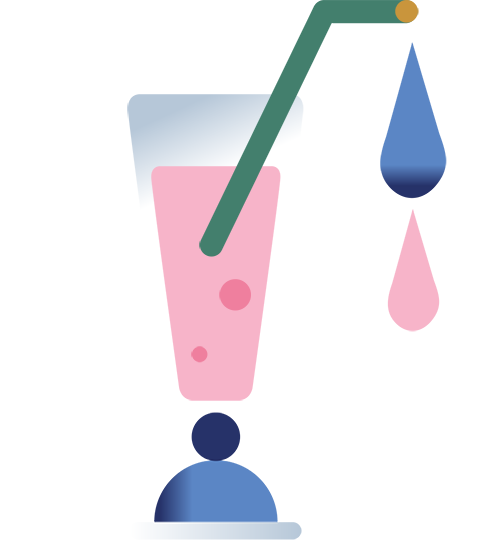馬提尼酒能報時。他們不能匆忙或浪費;你應該細細品味,一小口一小口地品嚐。馬提尼就像瞬間一樣,具有短暫的力量。“杜鬆子酒和苦艾酒的恰當結合是一種巨大而突然的榮耀;它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婚姻之一,也是最短暫的婚姻之一,”散文家、馬提尼酒使徒伯納德·德沃托寫道。“這種脆弱的狂喜關係在幾分鍾內就被打破了,從此以後就不可能再婚了。”這首歌和其他許多頌歌在過去幾十年裏積累起來,回蕩在諸如1947年在曼哈頓上東區卡萊爾酒店(Carlyle Hotel)開業的Bemelmans等酒吧裏。
“馬提尼是經典的,”酒吧經理迪米特裏奧斯·米查洛普洛斯(Dimitrios Michalopoulos)告訴我。“它給你的印象是你生活在過去,你生活在一個不同的世界。”大多數遊客來這裏隻是為了品嚐特製的馬提尼酒;在一個典型的晚上,有60到100人。那裏有穿著白色燕尾服、打著黑色領結的服務員,一個名叫厄爾·羅斯(Earl Rose)的家夥在小型鋼琴旁演奏爵士樂版的“Gymopédie No. 1”。牆上的壁畫是路德維希·貝梅爾曼斯(Ludwig Bemelmans)畫的,他以前是卡萊爾的房客,這個地方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同時,作者瑪德琳兒童讀物——描繪中央公園和曾經在酒吧表演的音樂家的場景。保羅·麥卡特尼多年來一直是這裏的常客;他喝的不是馬提尼,而是加了橙汁和菠蘿角的瑪格麗塔。酒保們招待他。
飲酒者對他們想要的東西很挑剔;對於馬提尼,人們關心的一直是如何。它們出現在19世紀末,1888年首次出現在調酒手冊上。原料是杜鬆子酒和苦艾酒,有時是苦味酒或curaçao。在一本新書中,馬提尼雞尾酒羅伯特·西蒙森(Robert Simonson)為《華爾街日報》撰寫有關飲料的文章《紐約時報》他解釋說,早期的版本很甜。“甜苦艾酒?”米切洛普洛斯不相信地說。“哦,我們不會問人們是否想要,因為那將是不同的東西。”
馬提尼幾乎立刻就流行起來,被文學和電影神話化,帶有詩意的觀察和荒誕的誇張,同時又懷舊。他們有高潮也有低穀。著名的歐內斯特·海明威永別了,武器“他們讓我覺得自己很文明。”冷戰期間,尼基塔·赫魯曉夫厚臉皮地說:它們是“美國最致命的武器”。它們變得越來越幹燥:根據文化評論家吉爾伯特·塞爾迪斯(Gilbert Seldes)的說法,在禁酒令時期,烈酒和苦艾酒的比例從四比一上升到八比一;1952年,次報道稱,“大規模的瘋狂,狂熱的崇拜”推動了幹馬提尼市場。馬丁尼遭到了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的攻擊,而傑拉爾德·福特(Gerald Ford)則為其辯護,他說:“三杯馬丁尼午餐是美國效率的縮影。”
有一段時間,馬提尼酒看起來岌岌可危;人們試著把它們加在冰塊上。90年代初,在俄亥俄州的雅典,一個名叫羅伯特·多諾霍(Robert Donohoe)的人開始關注這種情況,於是創辦了美國標準幹馬提尼俱樂部(American Standard Dry Martini Club),並出版了一份名為《馬提尼熱線》(the Martini Hotline)的通訊。多諾霍是美國標準幹馬提尼(純杜鬆子酒,不過他可以讓你順時針、逆時針或八字攪拌)的固執倡導者次,“伏特加馬提尼根本不是馬提尼。”羅格斯大學(Rutgers)教授洛厄爾·埃德蒙茲(Lowell Edmunds)將他稱為馬提尼巨人。埃德蒙茲撰寫了馬提尼卓越的曆史,出版於1999年馬提尼,直上90年代帶來了雞尾酒的複興——正好趕上了三杯馬提尼午餐的最後一場,其中很多都是在Bemelmans舉行的。
當你在Bemelmans餐廳坐下來喝馬提尼時,在為羅斯先生鼓掌的掌聲平息下來後,服務員會問你要哪種馬提尼。“杜鬆子酒,”你說。“什麼樣的杜鬆子酒?”對方回答道。“Tanqueray, Bombay Sapphire, Hendrick’s, Monkey 47……”服務員拿出一份有13種選擇的菜單(還有9種伏特加)。你忽略了一個事實:貝梅爾曼斯(Bemelmans)對“一杯馬提尼”加收4美元;亨德裏克的訂單是25美元。然後服務員問你喜歡嗎?“我們大多數人都喜歡喝幹馬提尼,也就是不喝苦艾酒,”米卡洛波洛斯告訴我。 None at all? “Nothing,” he confirmed. “In Europe it’s mostly gin and they always use vermouth. Here, it’s different preferences.”
人們點馬提尼的傾向可能是由於馬提尼的成分有多少,以及其中的重量有多重。我更喜歡苦艾酒。西蒙森解釋說,早期馬提尼的顏色與它的愛爾蘭孿生兄弟曼哈頓的顏色相似,因為當時的威士忌更淡,苦艾酒是琥珀色。奧格登·納什的"醇香的黃色馬提尼這句話就會被忠實地描述出來,而且不會太危險。幹酒的捍衛者可能隻會要求“小聲說”,這已經變得極端了:在50年代,發明了“苦艾酒霧化器”,可以在你的飲料中添加“霧”;60年代出現了一種類似醫療設備的“苦艾酒滴管”。還有一種久經考驗的技巧,就是往空杯子裏倒一點苦艾酒,攪一攪,然後倒出來。這對我來說還不夠,不過很難否認,太多或太少都會毀了一個夜晚。苦艾酒決定了你的命運:有難忘的馬提尼酒,也有不難忘的馬提尼酒,這與好與壞不是一回事。
“它總是在攪拌,除非他們要求搖晃,”米切洛普洛斯繼續說。(眾所周知,詹姆斯·邦德是錯的。)你可以加一點檸檬、橄欖(Bemelmans默認是三顆)或醃洋蔥。如果你不知道你想要什麼,你會得到酒吧的標準版本:伏特加,有點髒,加橄欖。有天晚上,我發誓我看到一個梳著馬尾辮的莊嚴女子喝著一杯加了橄欖和檸檬的馬提尼。
西蒙森要傳達的信息,就像貝梅爾曼斯和漢堡王一樣,是按你的方式來。他的書中包含的食譜既有曆史悠久的,也有富有創意的(Bar Goto的櫻花馬提尼(Sakura Martini),帶有微鹹的櫻花;Pegu俱樂部的Fitty-Fitty,那裏有多濕就有多濕)。他說:“每個人對馬提尼的看法都是錯誤的,因為每個人對馬提尼的看法都是正確的。”在合理的範圍內,我想,因為有發明,也有扭曲:比如,覆盆子馬提尼,戈黛娃夫人馬提尼。全國連鎖酒吧路易(Bar Louie)有一份“招牌馬提尼”(Signature martini)的菜單,其中包括“三葉草(200卡)”,含有Maker’s Mark、Courvoisier、龍舌蘭、“新鮮檸檬橙汁”和橙汁。我並不是完全的多諾霍,但如果我們不劃清界限,馬提尼的名字難道不會變得毫無意義嗎?當西蒙森談到類似的焦慮時,他聳了聳肩;這個名字並不總是指裏麵的東西:“杯子是東西,而不是飲料,”他寫道。(然後,他在書中把非傳統馬提尼酒的配方排除在外。)
玻璃很重要。在Bemelmans,一份三盎司的咖啡,大部分都倒進傳統的玻璃杯裏——一個帶柄的直邊錐形杯——還有一些裝在小玻璃瓶裏,再加一杯冰。人們通常認為馬提尼酒的本質特征是冰涼的,也就是那種冰冷的刺痛感。西蒙森的父親也是這麼告訴他的:“無論是感覺還是味道,馬提尼酒都讓人震撼。它讓你坐起來,集中注意力。”根據埃德蒙茲的說法,這種感覺也是杯子設計的一個功能:“這是一個很容易灑出飲料的杯子。”馬提尼是一種特權,一種責任,你最好看好它。
從這個意義上說,喝馬提尼就是體驗現在。馬提尼告訴時間,讓你靜止。他們不僅僅是渴望;他們自信。他們堅持讓你關注這個令人震驚的、扣人心弦的、令人不快的、充滿愛的世界。你不能把它們放在一邊。Per DeVoto:“你不能把馬提尼酒放在冰箱裏,就像你不能把一個吻放在冰箱裏一樣。”
貝特西莫萊斯是執行主編嗎哥倫比亞新聞評論。她之前在《紐約客》,哈珀,以及大西洋.
芭芭拉Malagoli是一位多學科藝術家,現居倫敦。
/cdn.vox-cdn.com/uploads/chorus_image/image/65355357/EaterDrinks_Martinis.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