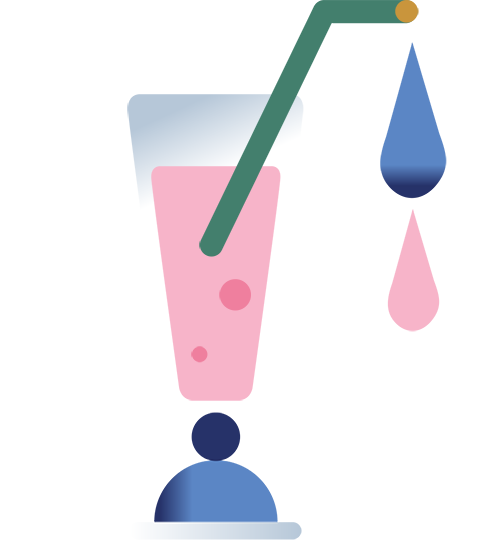在一個商場星巴克長島公路,我覺得我的裸臉衝洗。的刺痛了我的鼻子,然後房間模糊我的眼睛。在這裏,一個老人看報紙在舒適的椅子上我旁邊,我哭了。沒有人問發生了什麼事。我隻是哭了,孤獨的那一刻給了我第一個版本我經曆過幾個月。
有一個大的傳統在公共場合哭,特別是在紐約市,很難真正的孤獨。導遊一直在用最佳實踐;地圖已經標記的最佳地點。我肯定不是第一個指出,星巴克提供了一個更容易tear-friendly周圍空間(Twitter搜索短語“星巴克哭”收益有趣的結果)。這一切有關這一課題的文獻會讓你思維的一門藝術,但沒有:你隻是當你需要和希望沒有人幹涉。隻有少數的公共空間,可以依靠這種愉快的冷漠者,和星巴克是最普遍的。
早在2012年,一個個人的火藥桶,迫使女性氣質和剝奪爆發了最激烈的星巴克破壞我的生活。我是一個26歲的怪人伴娘厚的季節。盡管有全職工作,運行一個素食烘焙業務側喧囂、和生產沒完沒了的電子郵件,我與其他伴娘來證明有多好我知道我們共同的朋友,我放棄了咖啡。也許是明確的運行一個素食烘焙業務,我經曆的所有階段的健康:減少咖啡因,加入芡歐鼠尾草種子,每頓飯吃甘藍,某種程度上仍然汗流浹背的我對毒素在每日熱瑜伽課程。
伴娘會議組織去在茶黨新娘送禮會的細節。我們要讓帽子適合皇室婚禮。我的頭發然後幾乎被全部剃掉,所以我glue-gunned花皇冠而我周圍的每個人都激動地塑造精致的頭飾,湧軟磨硬泡,以及不加鑒別地深深沉迷於君主製和婚姻。深刻的疏遠,我發現自己渴望咖啡,毒素被定罪。具體地說,我渴望得到一個高的大豆雙冰摩卡。
我沉浸在wedding-industrial複雜後,我開車去星巴克,我的花皇冠騎槍,隻會稍微重新考慮我的決定貿易完美kale-fueled排便的甜救援厭煩的東西。但是我已經在那裏,所以我停我急忙進去。一杯垃圾不能撤銷數月的出汗和燕麥片,對吧?我下令,坐在和我一杯濃縮咖啡和巧克力糖漿,和哭了。
在星巴克,我隻是身體需要。哭有看報紙一樣可以接受。在那一刻,我意識到這不僅僅是經營企業的壓力,作為一個伴娘,我覺得壓力很大,而且我自己造成的對物理、政治和精神的純潔。糖和咖啡因削弱了我的痛苦,我感到了自由的婚禮戲劇,從我的烘焙企業,社會的期望。我獨自一人,在陌生人中,意識到我被一種自以為是的素食混蛋。幸福的準新娘,而是我在連鎖咖啡店是一個爛攤子。不過,六個月後,我的婚禮通過金屬吸管喝著一個綠色的果汁。
我曾經戴上綠色的圍裙,在我還在讀大三的時候,一個夢想的實現我自從我在1996年第一次走進一個星巴克。我是一個五年級生那麼渴望品嚐生活中美好的事物。我在郊區的孩子的心靈,星巴克代表彬彬有禮的博學與深色木材,烤肉和模糊的外國名字,和just-cozy-enough氛圍。當我在那裏工作,這份工作的報酬是每小時8美元,給了我噩夢的客戶出現在我的臥室的門要求白巧克力摩卡,但即使在一年後我辭職做辦公室工作,我仍然忠於我的第一印象。
這都是根據星巴克計劃來源於城市社會學家雷·奧爾登堡的“第三位理論。“他創造了這個詞在他1989年的書偉大的好地方,認為我們需要公共空間除了家庭(首先)和工作(第二位)作為功能的社區中心。奧爾登堡創建參數的廉價和開放的地方,可以有資格——教堂,咖啡館——注意到食物和飲料是很重要的,中立和安慰。還應該沒有人的地方有,密集的隻有那些行使自由意誌。
在設計、產品和服務原則,星巴克已經明確找到這個地方,稱員工”的合作夥伴。”雖然很多人嘲笑為糟糕的服務定價過高的咖啡,你可以得到一個高杯約2美元在紐約,即使所有的錢你得花一天,咖啡是一樣的一些金融家夥可能會使七位數。鏈,在尋求這個中性的,邀請,已成為實際場地為第三位和安迪·沃霍爾的可口可樂哲學:“可口可樂是可樂,再多的錢能讓你更好的可樂比屁股在角落喝。”
不知何故,星巴克是公用的,而且通常有抱負的和無害的,一個完美的表達第三的位置。這就是為什麼,當一個白經理在費城警察兩個黑人坐在一個等待他們的朋友,這是一個巨大的侮辱了公司理念,8000家門店因歧視培訓還管轄規模的一個下午。
這也是為什麼,當一個人覺得很垃圾,他們可以去最近的星巴克咖啡哭。每個商店促進匿名的千篇一律,而資產階級做作是柔和的。“當你需要哭泣,你打算去Dunkin ' Donuts或星巴克嗎?“最近一個熟人問,修辭,因為答案是顯而易見的:星巴克照明不太嚴重,一方麵,也邀請你不僅僅隻是一個事務性的甜甜圈。星巴克想要你坐下,把舒適、打開紙——也許有哭,他們判斷是誰?美國可能運行在一個,但感覺舒適的哭泣,故障是否對某事做伴娘一樣輕浮或嚴重疾病的親人。
居住在弗吉尼亞州的一個朋友告訴我,當她的丈夫接受癌症治療,她發現洗滌早餐連鎖店。“我很少進入星巴克,坐,但是一旦我去和我的女朋友之前每天6:30到醫院連續20天,我丈夫的腫瘤切除手術後,”她告訴我。“我個人脫離我們的地獄,我們生活在和哭泣而吃羊角麵包拋錨了。星巴克是在去醫院的路上對我來說,就我個人而言,當我開始去那裏的時候,感覺就像一個迷你打破這一切。”
另一個朋友告訴我如何,當她的第一個大學和她女朋友分手了,她去了時代廣場的位置。“我命令一個巨大的星冰樂,公開抽泣著太長時間在什麼可能是最混亂的星巴克在美國,”她說。“這是奇怪的是安慰崩潰,沒有獨處但仍然是完全匿名的。”
而企業巨頭追逐newer-wave咖啡店的趨勢,或許有一些很酷的孩子可以學習,如果他們想吸引顧客在他們最低的時刻。沒有更好的辦法,似乎成為一個固定在一個人的生活盡管higher-minded意圖比提供一個空間裏哭,同時驗證檸檬塊。剛有什麼好處,single-estate咖啡在一個別致簡約咖啡館如果你不能輕鬆鹽與你流淚嗎?他們可能試圖贏得我們在冰冷的啤酒,但是星巴克知道真正俘獲人心的方法是讓我們哭泣。
/cdn.vox-cdn.com/uploads/chorus_image/image/61263785/la_eater_CR_v02.0.png)